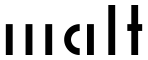“安娜贝·赛尔多夫的成功, 为过去20多年流行的明星设计师和外表狂野、夺人眼球的建筑提供了一个反例。”
建筑设计师安娜贝尓·赛尔多夫(Annabelle Selldorf)在汉普顿一处海滨房产的施工现场巡视时,显得有点蹒跚。一天前,她拉伤了后背,但仍尽力开车从纽约的办公室赶过来 ,到这处近期刚接手的项目检查进展。这是一座总面积近1500平方米的房产,带两个泳池和一部电梯。赛尔多夫穿着牛仔裤、笨重的棕色Bloundstone靴和一件绿色绗缝夹克,她小心翼翼地绕过一堆堆钢筋和工程设备,偶尔对着她的柯基-拉布拉多混血狗尤西吹声口哨。
她对看到的情况很满意,只有一处例外很烦人:从前的房屋那片已被拆毁的基地留下了一堆零乱的瓦砾和垃圾,有待她的团队处理。“这里面混杂着疯狂的无知、难以置信的傲慢,还有——什么?”她冲一帮人问到,其中有建筑承包商和两名来自以她命名的公司的建筑设计师。“想省点儿钱?”建筑商问。赛尔多点点头。“就是。”她边说边返身向自己的车走去。
赛尔多夫不喜欢浪费,无论是在一栋建筑的施工现场,还是在它被拆后的废墟里。她的风格,时简约而又微妙地呈现出奢华—一个赛尔多夫的经典改造手手笔,时那种只有一场细心的参观者才有可能注意到的设计,例如坐落在马萨诸塞州威廉斯敦的斯特林和弗兰锡恩 克拉克艺术博物馆。她于2014年对其进行重装,微微调整了各扇门的位置,这样,参观者在向某间展厅里凝望时,就可以仅见画作,而看不到其后相连的其他房间了。这是一处改变了整个观展体验的小细节。
赛尔多夫设计的建筑也一样节制,而同时它们内部的配套设施都极其奢华。在纽约的哈德孙河畔,一栋2011年完工的19层高楼配有一步汽车直梯,可以将业主们的汽车直接送上他们所住的楼层,这部电梯位于楼体的一侧,与楼并排。建筑正立面上的双层挑高窗户,被一格格小窗框分隔开来,使得这栋建筑看起来比它的实际规模要小一些。“我门试图实现一个每部分都被明确解析过的综合体,令你无法再从中删减任何东西,”她说,“但同时,每样东西又能以一种独特的和谐,搭配在一起。这就像对一个句子反复推敲,直到再没有更好的表达方法。”
那些把钱花在建筑上的富有人士、公司和城市,并不总是那么看重品位和谨慎的态度。在纽约,等到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设计的那座世贸中心交通枢纽于今年内竣工时,其总开支将达40亿美元——比计划晚了6年,且花销比预算近乎翻了一倍。“同所有的艺术形式一样,建筑设计也有其相当摇摆的一面。”《纽约书评》的建筑评论人马丁·菲勒说。本世纪最初10年时诸如卡拉特拉瓦、弗兰克 ·盖里、丹尼尔·李博斯金这些巨匠级人物,以及一众“明星建筑师”呼风唤雨的时代。他们用玻璃、钢铁和水泥,构筑起从物理角度几乎无可能的狂野建筑。菲勒说,现在大势摆向了赛尔多夫的风格。“她知道一位非常独特而有见多识广的客户,想要的是什么。在这个如此巨额的财富掌握在如此有限的人手上的时代,任何事都有可能。”
过去4年里,赛尔多夫的公司在纽约完成了3栋豪华公寓大楼项目,并有另外4栋正处于设计或建造阶段。她在汉普顿已经完成了10栋房屋,还有6栋正在建造。她还为布朗大学的约翰·海图书馆及纽约的新画廊博物馆改造了内部装潢。去年,她在竞标中赢得了圣迭戈现代艺术博物馆一处占地近2800平方米的扩建工程;此前一年,她还接受了制药巨头女继承人、亿万富翁马娅 霍夫曼的委托,在法国阿尔勒市将一片占地近5400平方米的破旧工厂库房,改建成了luma基金会的一处展览空间。
赛尔多夫现年54岁,生于德国科隆,在上世纪80年代初移居到纽约。其定位恰好跨在自在的无名氏和业界明星之间。她的个人风格时无可挑剔的极简主义。她佩戴者一块不锈钢男款劳力士表,开着一辆略有磨损的奥迪全路况旅行车。她的伴侣汤姆·奥特布里奇(Tom Outerbridge)住在格林威治村的一套两居室公寓里。她是在为布鲁克林的落日公园社区设计一处回收厂方时认识他的(他是那家工厂的总经理)。不过,他们的之所可并不低调——其中摆满了雕塑,从唐纳德·贾德的一个小件到有600年历史的高棉残片。在纽约的社交界,塞尔多夫也成了一名杰出人物。去年那场名流云集的新博物馆春季晚宴(New Museum Spring Gala),就是向她致敬的。她的面孔会时不时出现在媒体的派对专栏中,配上其与家政女王玛莎·斯图尔特在广场酒店橡树厅,或是同艺术家辛迪·谢尔曼在威尼斯一个派对上的合影。
塞尔多夫本人很有魅力,她身上兼具着一股毫无敌意的聪颖,和一种怪异的幽默感,有时很难搞清她是不是在开玩笑(“几年前我确认了,说反话是对冷嘲热讽的一种合适的而替代”在从汉普顿驱车返回、走在长岛高速公路上时,她直视着前方说道)。讲着一口微带口音的标准英语,时常在话语中插入些自我贬低。“没有一件事会如你预期”她谈及自己的建筑设计,“当意外发生时,你所能做的就是尝试着别变得歇斯底里”
塞尔多夫的事业,为过去这20年里出现的多数建筑提供了一个反例。在这一时期,帐篷形的建筑设计项目被视为获得经济复苏和城市声誉的关键。这是一个被称为毕尔巴鄂效应(Bilbao-Effect)的概念,指的就是盖里在西班牙北部设计的呈波浪状、外表覆钛的古根海姆。这座竣工于1997年的博物馆,将那座死气沉沉的航运小镇转变成了一处艺术爱好和钟爱的旅游目的地。根据毕尔巴鄂当地政府的数据,在博物馆刚落成的头3年里,有近400万名游客到访,为当地经济贡献大约2亿欧元产值。
全球各地的艺术机构、大学、城市几公司纷纷抓住了这个兴旺繁荣的保障。吸引研究的建筑物,空降到了一些不太可能的、往往破败杂乱的地点,成为新闻头条青睐的、代表着品味与设计的灯塔。比如卡拉特拉瓦设计的额造价1.22亿美元的密尔沃基艺术博物馆,以及扎哈·哈迪德在中设计造价2亿美元的广州大剧院。
“看看理查德 迈耶在巴塞罗那设计的现代艺术博物馆,”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及考古学教授哈尔·福斯特说,“它就像一艘宇宙飞船,降落在一片工薪阶层住宅区里。”
但是,这些建筑的委托人很快就意识到,来自明星建筑师的保证很多时候难以兑现。于是官司就一桩桩来了——麻省理工学院状告盖里,他设计的一栋造价3亿美元的研究楼存在渗漏;还有西班牙的瓦伦西亚市起诉卡拉特拉瓦,在他所设计的造价10亿美元的艺术综合体中,那座歌剧院的天花板不断脱落,致使其下方的街道无法通行。其他客户则发现,仅仅建起一栋建筑是不够的;他们还需要在里面填上些东西。“就像哈迪德在罗马设计的Maxxi楼,”福斯特说道的,是一座最终造价比预算超出了1亿美元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在建筑物上投入了那么多钱,为展览项目余下的资金就不够了。它落成不过几年的时间,就已经深陷困境。”
塞尔多夫搬到纽约后,很快去参加了普拉特学院的建筑设计项目。毕业后,她在极简主义建筑师理查德·格鲁克曼的办公室工作了一小段时间,搬到意大利呆了一年,然后回到美国,开始出来自己单干。“我有各种各样的想法,而且我真的不乐意再为他人工作了。”她说。一位朋友雇她装修一间厨房,于是她“赚了些钱,足以支付几个月的房租,并维持我那非常自律的生活方式了”。接下来的而一份工作是,“我不知道,一个厨房和一个卫生间或什么的”,她说。她的公司——塞尔多夫建筑事务所(Selldorf Architects)于1988年正式成立,发展至今。
赛尔多夫最为知名的早期作品集中在艺术画廊领域。她的第一个项目是给迈克尔·沃纳做的,其位于纽约东67街上的艺术空间代理了诸如乔治·巴泽利茨和彼得·多伊格这牙膏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家。接下来是为大卫·茨维尔纳做的项目,其画廊被普遍认为是全世界第二有实力的(第一位的是高古轩画廊,赛尔多夫也曾为之工作过)。事实上,国际顶级画廊接踵而至:格莱斯顿画廊;让她设计了纽约、伦敦和苏黎世办公室的Hauser&Wirth画廊;绅士,高贵堂皇的阿奎维拉画廊也于2008年时请她装修了上东区的一栋宅邸,那是画廊自1967年起就拥有的房产。
“从前的艺术圈并不像现在的样子,”赛尔多夫在谈及早些年时说,“我们都在共同成长。”对于茨维尔纳的项目而言,这是句实实在在的描述。两个人同样来自科隆,不过,据茨维尔纳说,他们是在他15岁来纽约学习一年时认识的,赛尔多夫当年18岁,刚刚进入普拉特学院。1992年,当他于苏豪区的格林街开设自己占地近150平方米的第一家画廊时,“她的公司那时候只有两个人,而我只有一个人。我觉得她甚至都没有要我的钱,” 他说,“她就是很高心能做点事情。”近25年过去了,茨维尔纳说赛尔多夫已经为他设计了15到20个项目,从“小到一段台阶,到在第20街上为我建造一整栋新画廊。”
 很快,赛尔多夫进军博物馆项目。2001年,她在第五大道上为近画廊博物馆改造了一栋布杂学院式(Beaux Arts)的大宅,专用于陈列亿万富翁罗纳德·劳德的德国及奥地利艺术收藏。“那栋建筑本身相当普通,”菲勒说,“而她仅用寥寥数笔,就令它看起来好像专门为那些艺术品而建的了。”
很快,赛尔多夫进军博物馆项目。2001年,她在第五大道上为近画廊博物馆改造了一栋布杂学院式(Beaux Arts)的大宅,专用于陈列亿万富翁罗纳德·劳德的德国及奥地利艺术收藏。“那栋建筑本身相当普通,”菲勒说,“而她仅用寥寥数笔,就令它看起来好像专门为那些艺术品而建的了。”

自那时起,赛尔多夫进行室内装潢设计或改造的项目有:一家专门展示玻璃制作工艺的威尼斯新博物馆Le Stanze Del Vetro ;为2013年的第55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对威尼斯军械库所做的调整;纽约的圣经艺术博物馆;以及威廉斯敦的克拉克艺术博物馆,该项目自2007年起开工,首先改造了原有的建筑,然后又在一墙之隔建起了曼顿研究中心。
赛尔多夫在威尼斯的作品之所以引人注意,只因那时在美国之外的案例。她同很多知名建筑设计师不同,并不在国际上广接项目。比如,她在中国就从没设计过一栋楼。他说, 这是自己公司的风格和行为方式所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
“人们吧中国当成了一个成败无定的试验场,但那些东西无疑都是非常稀奇古怪的,”她说,“有时我觉得自己有点欠缺,因为那不是我最想要做的——尝试新东西。并非我不喜欢尝试,而是因为我觉得那很浪费。”
对于她的很多美国客户而言,这种态度就是一个买点。她的审美观,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高雅的选择,以替代过去几十年间的浮华风格。“她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仍然从里到外做设计的建筑设计师,”房地产开发公司Urban Muse 的所有人格劳科·洛里-盖蒂说,他的公司聘请了赛尔多夫在纽约建造三栋豪华公寓大楼,“她非常优雅,她也非常深思熟虑,而且她能把一处空间分割得令我耳目一新。”洛里-盖蒂的公司,就是赛尔多夫在切尔西住宅区那栋带汽车电梯的大厦背后的投资商。这栋大厦从最下方4层往上,向里锁进,那4层的表面还覆盖了陶砖,从而传递给经下方路过的人一种,这座巨型建筑也很符合人的尺寸的错觉。“建筑也不一定要难看,”赛尔多夫说。“没必要把它做得难以入目”。
赛尔多夫交付项目既守时又合乎预算,这在她的专业领域里时很罕有的。“她所谓一个知名设计师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她真的很在乎客户。”施坦威公司的主席麦克·斯威尼说,也正是他,选中赛尔多夫来设计位于曼哈顿中城区的是施坦威乐厅。“她凭直觉就知道该如何钢琴布光,如何使它成为这个空间里的主角,”他说,“有太多时候,设计师把自己的建筑弄成主角。”
她的公司规模之大史无前例,而其位于联合广场的办公室则毫不招摇。走出电梯,访客就会来到一处小型等候区,那里的两把椅子上方,挂着三幅著名概念摄影师贝恩德和希拉 贝歇夫妇的黑白照片。公司有一间会议室、几间由玻璃围住的办公室,以及一个接待前台。走过转角,开放式的空间就开阔起来,其中有排一条街区那么长的办公桌、电脑和落地式书架。
公司雇用了55位建筑设计时和10名办公人员。根据美国建筑师协会的统计,这一规模已使之跻身美国前3%大的建筑事务所。只有17%的美国公司有女性所有人或合伙人。即便她的性别时一个妨碍,赛尔多夫也不会承认。“经验的作用和性别一样重要,”她说,“要想得到比我们做过的案例更大的项目,总归时很难的。我们受阻时因为我们是女性吗?我不这么认为。”
她继续拓展着项目规模。2013年,她完成了占地4.45公顷的大手笔——日落公园的材料回收设施,也就是位于布鲁克林的那个回收厂房。其中1.3万平方米的西姆斯楼,凭借其设计和施工赢得了公共设计委员会颁发的优秀设计奖。



在她所有作品当中个,赛尔多夫队这一个尤其感到自豪。那可能是因为就是在这个项目中她遇到了自己的伴侣奥特布里奇。不过,这栋每年回收20 万吨塑料、玻璃及金属的西姆斯楼,也使她从国际艺术届的奢华当中偶得解脱。
“有几件我们目前正在考虑的事,包括保障性住房,”她说,“我非常期待将它做得和其他住宅一样好。”对赛尔多夫而言只是个机遇,以体现出她对氛围、客户和施工的重视,并不是只对亿万富翁才奏效的原则。“有时候为使自己冷静下来,我会说,’已经有那么多糟糕的建筑了’,我可以做得比那好一点。”
By《Bloomberg Businessweek》
撰文 James Tarmy 翻译 吴燕